 中传云资讯系统
中传云资讯系统南方观察 | 生命与情感的表达式——作家周碧麟散文管窥并代序
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人们更喜欢直接对意义进行阐释,然而意义不仅来源于内容,也源自边界不那么确定的形式以及内容与形式所产生的意味。由是也可理解为对形式的独特把握,所有的艺术文本都是过去时的艺术历史,也就是说,一个新的艺术文本,它只能按照自我方式生长,以鲜明个性完成自我论证,进而立足于艺术之林。那些遵循或尊崇既有艺术形式的复写,如果成为不可逾越的过程或令人敬畏的某种范式,很可能就成为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艺术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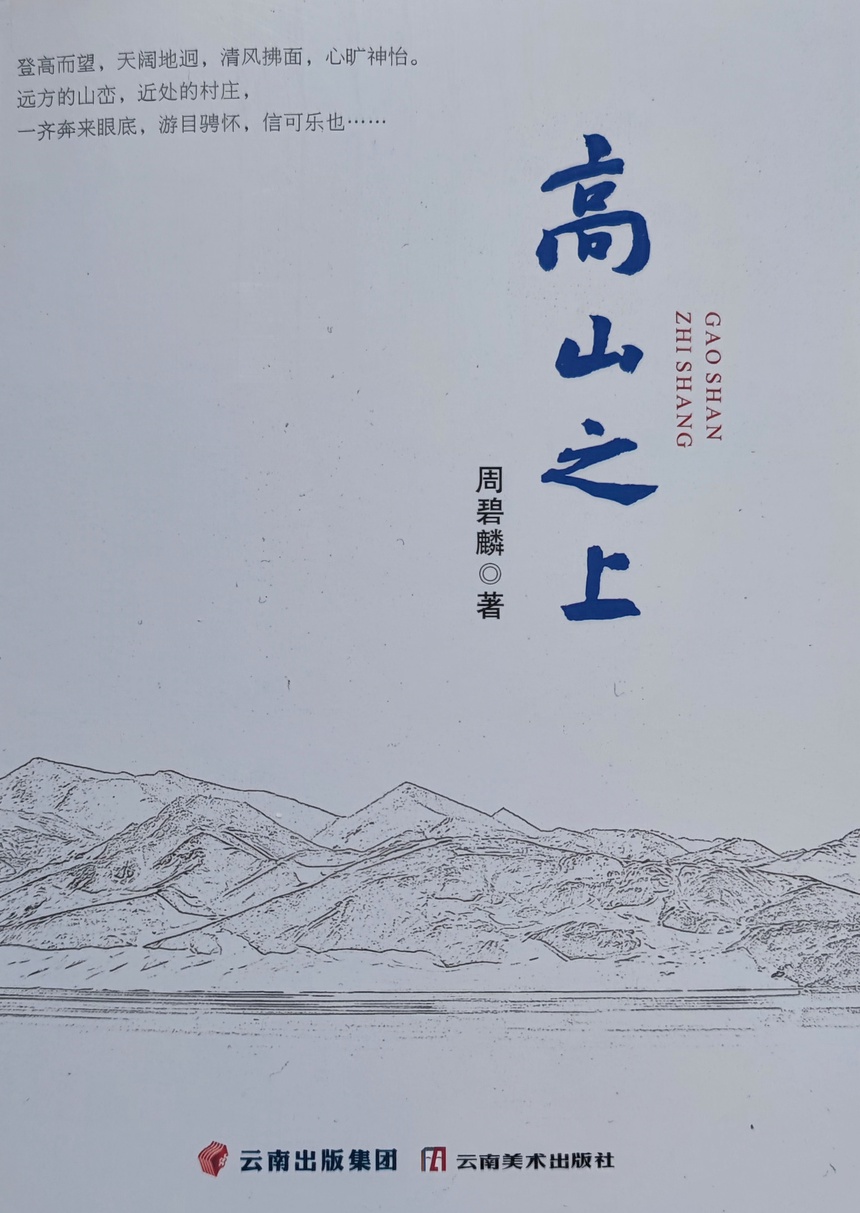
周碧麟散文新著《高山之上》
引发我作如是思考的,是在阅读湖北作家周碧麟散文新著《高山之上》时,再读了他此前出版的三部散文集,使我对他在散文创作中自然沉静却又求变的抒写有着独特感受和不少触动。周碧麟的散文,立足现实生活,以人为中心,以爱为出发点,以情感为显影剂,以民族为底蕴,以时代为羽衣,以生命为归宿,质朴而真诚表达着自己的所见与发现。在他的笔触下,人与世界的种种相处,仿佛蕴含于生命与情感的函数表达,而在这个属于他的表达式中,爱与情感互为导数,让人感触到生命激荡的华彩与哀伤。
作为长期生活在鄂西的土家族作家,他以开放视野、开掘姿态和独特笔触写出了独到而深长的生命韵味,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中土家人的心灵史、情感史和发展史,使我对文学的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有了更为丰富的想见与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和思考周碧麟的散文创作,不仅对于他个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也能为研究土家族文学在新时代的特质和发展增加必要的观察样本。
一
周碧麟在老家的生命历程,与老家的山川恩泽,与继母的人间温情,以及村庄的风情民俗,他都在散文中进行了真情抒写、生动呈现。
2019年,在送走继母处理完老屋后,他和全家人在那个生养他的偏远地方失声而哭,从此那个叫周家包的故乡再也没有周姓人家。然而,生长于周家包的周碧麟却以另种方式,将这个去处烙印在精神河流之中,未来周家包仍可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在数字化数据世界被打捞浮起,以某种今天尚难预测的方式回到现实也未或可能。当然这种村庄志或人物志式的抒写,并非他的首创而是由来已久,他在众多类似抒写中能有不同,极为重要的是,他用难以精确描述的爱完成了和继母之间关于生命与情感的表达,这种表达是独特甚或是稀缺的,他笔下的继母成为散文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在此基础上,他尝试完成由爱父母向爱家乡爱生活爱大地的延展与转换,爱由天性使然成为人之内在自觉。因此,在周碧麟最初的散文创作中,家乡、亲情等传统主题是他的重要写作资源,在他生命里的那个村庄中,风土人情、牲畜用品、山川树木都是他抒写的对象。
在《中溪走笔》一文中,他深情发掘了故乡中溪村的人文精神与历史记忆。在他的笔下,在这个小小村庄中,不仅有第一位全国党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也有第一位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第一位全国作协会员,还有第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第一位知名职业经理人和第一位全国网红好人。同时,这个村庄也极具历史人文内蕴,其间的花屋场既是历史上“八秀才之家”和白莲教首义之地,也是大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府的红色处所,而流传于民间的腰磨岩、牛抵岩、黄金藏、五不怕坟等传说,赋予这个村庄极强的传奇色彩。不仅如此,这个村庄还有独特秀丽的自然风光,公路挂在绝壁犹如大山腰带,皓月穿过山腰巨洞宛如追光投射田园瓦舍,村庄的自然风光也美妙绝伦。可以说,乡村乡情的打捞与抒写,是周碧麟散文创作初始而核心的精神资源,奠定了他散文的淳朴格调和自然气韵,也成为他审美建构的策源地。也是这一精神资源,进一步链接了他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关注与提取,因而他笔下的乡村,不仅是一个亿万斯年的风化遗存,也是一个人们在交往交流中积淀的人文乡村,还是一个隐含种种传说的神化村庄,寄寓着一个民族内在而共同的审美情韵。
在抒写家乡和亲情之外,周碧麟的笔触伸向了大好河山,源于他面向世界的旅行,他的散文也因此呈现出更新的开阔气象。他从国内行走开始,进而游走世界各地,饱览美好河山,品味不同文化。周碧麟的行走,基于他长期在大山中生活,外部世界带来的反差激发他的新奇与共鸣,为此创作出不少有关行走的游记。
在《走不出你的情怀》这部散文集中,他以“远山近水”为辑,初次把笔触伸展到土家山寨以外,继而以《远方何处》整部书,专门记述行走世界,品味各地民俗风情,饱览大自然美妙风光,这既是生命历程的美好记录,也是自由情感的倾情浇注,展现出奔放达观的生命意趣。在《高山之上》这部散文集中,依然能看到这种行走的自觉延续,他在追求梦想中不断分享着发现与见闻。这种关于旅行的文学写作,经过发育逐渐形成一步一景、文化发掘等传统,也衍生出高度商业化的“指南文学”。
旅行文学要具备品相和质地,必然还是要回到文学创作的初衷,将旅行作为题材来加以处理,犹如《老残游记》对“游”的开掘。显然,周碧麟在处理这些旅行时光与记忆时,是有斟酌和考虑的,笔气纵横中写出了一些新意。纵观他的旅行文字,不仅注重对城市景物的描摹,也重视对异地文化的发现与挖掘,既有情感注入又有文明碰撞,既有拥抱也有思考,展露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生命格调。
在《能不忆疆南》中,天山风物不仅是大自然恩赐,也是富有神奇和磁性之处,他从中感受到现实、历史和人文的交融与洗礼,是对生命的一次涤荡。在《远方何处》这部书中,他的目光真实地从数十个国家的不同城市掠过,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也震荡着他的情感,使他对现实生活有着更深理解。在这些有关山川风物和不同民族文化的散文中,可以明显体味到周碧麟散文气象的某些变化,相较于早些时候的乡村风情散文,这些旅行随笔视野开阔,笔触愈加活泼轻巧,情感愈发深沉浑厚,直接影响到他对现实的介入,触动他在题材选择上走向现实和宽广。在《岁月静悄悄》这篇后记中,他表达了这种逐渐获得的体悟:一个人所认识理解的世界永远只是他看到的世界,许多曾以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原来还会有许多别样的答案。这种感性体悟,很可能也不单纯来自于行走,还来自于故乡与世界的碰撞,来自于固执中生发出的平和与热情。
周碧麟在回望与行走中也保持了对时代大潮的拥抱,从他的四本散文集,大致可以体味到他与时代大潮同频共振的内在欣喜与淡淡哀伤。一方面,无论是回望故土还是行走江河,也无论是挖掘文化还是凝望风情,它们都带着时代之光弥漫出新鲜气息,即便那些老旧事物也因此而照耀一束今日之光,使人在历史回响中总能触碰到当下而思绪流淌。另一方面,他在散文叙事传统上走得更热烈坚定一些,有意融入火热的现实生活,以记录者姿态敏锐捕捉当下印象深刻、令人感动的事件,细致叙写发生发展历程,提取事件中隐藏的人性光芒,扩展内心涌动的喜悦与温暖,写出了一组叙事抒情兼具、向非虚构有所拓展、具有饱满现实情景、饱含浓烈情感的纪实散文。这类作品紧扣时代主题和重大事件,既有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也有艰苦卓绝的抗疫,主要包括《爱在清江流淌》《春风化雨润板桥》《决胜佑溪》《谁在点亮群山》《一位土家工匠的追梦人生》《高山之上》《山里有座山》等作品,莫不闪现着明亮的时代之光。
《爱在清江流淌》中,驻村书记和村民们在疫情中用行动诠释了人与人之间另种真情,曾经是医院职工为村民捐款义诊、减免住院费用,疫情爆发时村民们自发将自产的生活物资日夜兼程送到医院,其间的村民李承池夫妇用两天一夜时间打了十七箱豆腐送给抗疫医护人员,令人感慨万分。这组文章中,糕点师傅在传承创新中不给师傅丢脸的坚守,佑溪村破解“芝麻开门”秘咒的艰难求索,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努力与奋争等,周碧麟无不给予莫大关注。在他饱含深情的笔下,他们是驻村书记、支部班子、治保主任、回乡创业者、专业养殖户等,是这个时代最美丽的建设者与奉献者。从这些作品中,能够感触到大山奋争与嬗变的轨迹,看到干部与村民的淳朴之情,由此也体味到周碧麟对家乡在历史变迁中的深情关注和深沉眷恋,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家乡、为改变贫困与落后的人们而吟唱、助威、加油,这些文字有时候急切得近乎报告文学,有时候又热烈如散文诗,却因发自肺腑的真情而充满诗意,读来令人动情不已。从这组文章中,也能看到一个散文作家对现实责任的坚守,对现实生活介入的生动表达。
二
面对丰富的创作资源,以活动器物等展现民族特征,是周碧麟萃取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路径。土家族的民俗文化风情,主要由丰富的各种文化、习惯、心理等综合构成,典型如巴山舞、跳丧鼓、山歌、南曲、故事、杀年猪、忙年等等,都成为他潜心开掘的对象。然而一地的民俗文化风情,又远不止于此,一些如哭嫁、赶仗、纳鞋、杠神等生产活动和幺门、火垅、吊脚楼等器物用品也莫不内蕴民俗风情,在《做山货》中,他讲述了剥构树皮和割棕片的生产活动,割棕用的刀子这一器物至今还收藏在书柜里,让他在铭记苦难中学会珍惜。
我印象很深的,是周碧麟在《土家火垅记事》中写高荒人的独特茶道:一个拳头大小的土罐,在火塘边烤得红烫后放进细茶,轻轻簸动到茶罐发出焦香,加滚水时一股白气直冲而出,直到茶熬得像膏子,主人才小心端起茶罐细细滗出半杯,双手恭敬递给客人。同样是在这篇散文中,还写出了山村女人雪夜围火取暖时既息而作的情景:杨幺姑和母亲在昏黄的桐油灯下边对唱土家情歌,边抽动纳鞋底的索子,墙上舞动着手臂的影子,像演皮影戏般如梦如幻。
土家族民俗文化是极其丰富的,大多已经被写进各种典籍中,但也还有一些像璞玉埋在岁月深处,需要去寻找、去发现,去辩识。周碧麟就是这个自觉的发现者和记录者,在对土家族文化的长期观察与体验中,他对民族语言形成独特感知,对巴土文化有着极大热情和极深感触。在那些拥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其民族语言能够通过民族文字予以精确传达,艺术家能直接选用鲜活的民族语言,哪怕这种语言对于其他民族而言在交流理解上存有一定困难。但是,对于只有本民族语言却无本族文字的写作而言,如何内在地展现民族特质和文化内涵,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探索与思考。面对土家族没有文字的语言,周碧麟并不刻意去突出模拟文字在语音上的民族性,而是从风俗、活动、器物等方面建立民族文化的磁场,既保留民族文化的腔调与韵味,又注意跨民族的融和与共通,极大地增强了文字表现力。相较于音乐戏剧等艺术门类,这种对语言文字艺术的处理方式,我认为颇为合适得体,也很值得参考借鉴。

散文新著《高山之上》作者周碧麟
在生活环境中对文字加以运用,注入个性化获得情感力量,是周碧麟散文语言常用的处理手法。在长期执教中,他积累了良好的语言文字功底,尤其在古汉语方面更为纯熟,使他对传统文化有着很深体会。他深谙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使文字通过文化环境进入语言应用而得到滋养。这种对语言的处理,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他的散文创作之中,他的某些创作笔法,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一位老旧文人之笔。想来,我从他文字中获得的醇厚感,就来自于生活事实与民俗风情的熔铸所展现出明亮的个性之光。这种个性正是文章暗含的密码,纵观他的四部散文集,无不有着独到的语言传达、自觉的民族文化融入和纯粹的情感浇注,由此而酝酿形成独特味道。
我一直认为,虽然极少作家具有语言天赋,但文学语言是可以习得即在阅读和写作中逐渐获得的。对于大多数写作者而言,即便也有一定天分,持续的后天习得才是重要的抵达途径。在长期积累中,周碧麟对民族民间文化情有独钟,他常常情不自禁地抖出民族文化“包袱”,使他的表达具有肥沃的土壤和生长的动感,让人能嗅到空中弥漫的腥辣、硝烟、山野等浓烈的烟火味道。
在《生命之舞:土家撒叶儿嗬》中,通过对土家族民族风俗跳丧鼓的回忆,展现的土家族人以审美面对死亡、以歌舞表达感念的通脱旷达与宽阔胸襟,正与他的传神叙述相得益彰。将内在情感熔铸到文字之中,往往既见秉性又见功底,实现殊为不易。世间事物千般万种,唯独人之个性与情感,始终在同于不同中生长,最是令人难以说清道明,这对于文学而言也正是开拓空间所在。将难以表达的人性情感细致深刻地揭示,需要作家对笔下每一个文字赋予灵魂,使文字从意义的精确走向意蕴的无限。
周碧麟在情感熔铸上自有特点,他写年事已高的母亲从乡下送土特产进城,豆腐已被拌成了肉价,对周碧麟而言爱是对母亲疼痛的成全,这种情感质朴单纯;而对于母亲而言,爱是儿女无私的奉献,情感也是单纯质朴的。当周碧麟将这两种单纯质朴归置到一起时,文字便如两列相向而行的高速列车具有强大的情感震荡力,人间之爱又岂可一语而概括其全部?显然,周碧麟并未将他拥有的语言功底华丽运用,一如他所追求的平凡人生,他为文字加持个性化情感展现的语言魅力,正是我在阅读中所体验到的独特韵味。
塑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是周碧麟擅用的表现手法。我对周碧麟散文的深刻印象始于多年前他的《又是一年菜花香》,他将自己的真情与继母的深情融合在一起,写出了一位浸润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母形象,这个继母形象犹如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深深刻在我的脑海。
通读周碧麟的散文,可以看到他以叙事手法真实鲜活地描写了继母、父亲、二爷爷、女儿、外婆、舅舅、高老师、伯父、二妹、鼓师、举人、哈哥、糕点师傅、扶贫干部、返乡青年等各类人物,这些人物都生活在当下不同的现实情境之中,既有大多数人的共性又有着鲜明个性,都携带着作者的情感基因,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
他在写一位外号叫举人的人钓鱼时,有人问钓了几条,举人回答说“这条钓上来,还钓两条,就有了三条。”举人形象顿时跃然纸上。在散文的叙事传统中,受形散神聚等理念影响,散文选择的往往是间断性叙事,东鳞西爪或神来之笔,尤在一些短章中比较显见。
近些年来,以家族记忆、历史沉钩等为代表的长篇叙事兴起,散文叙事向遵循事物线性逻辑的纪实方向发展,与报告文学、非虚构的边界模糊不清。周碧麟写散文的叙事冲动,往往从对细节的白描开始蓄积,从对细节的描摹刻画到对事件的整体把握,不时将小说手法在散文中予以运用,不仅从细节中获得情感力量,也从事件中加持情感力量,很是令人眼前一亮。
《柿树的故事》中二爷爷早就准备好临终“装老”:他上下穿戴一新,脚上穿着一双绣花布鞋,一根指头粗细的棕绳子勒进他的脖颈,他仍然像平日那样谦卑地低着头。周碧麟笔下的这些现实人物,与小说家塑造的人物形象极不相同,他们不强调典型化而追求个性化,每一个人都散发着爱的光芒,这种爱正是从母爱开始,随着生命成长而不断扩展。而无论所爱之人还是被爱之人,都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不代表别人也不代表别的意志,他们首先代表极其平凡的自己,透过周碧麟的笔触,在平凡中显现温暖和智性。这些笔下一个个平凡的人物,不也正是一个个平凡的我们的缩影么?
三
总体来看,以我手写我心,自然率性地表达对自我感觉的唤醒与确证,可以看作周碧麟散文的重要特征。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无非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大空间,对物质世界的理解与阐释,当只有在基础研究中才能逐渐窥探到一些自然奥秘时,这种探索越来越属于极少数人的事业,而对精神世界的感知虽则属于每一个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将己情传神于对象,由此打通物质世界和感觉世界。当把这个感觉世界用文字方式进行表达和呈现时,它就是文学。
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感觉世界与物质世界真实性的讨论,如果将人的所有理解与事物存在要划上等号,这种讨论就失去了真实性的前提。我们可以理解真实就是客观,但人所面对的真实的本质是真实性,它既是物质世界的固有本质,也是感觉世界的动态特性反映,真实就摆在那里,我们从来只能无限接近它,我们所把握的,永始终是人所理解和赋予的真实性。这就为不同个体对感觉世界的把握提供了丰富的空间,真实性的“性”来自于不同而丰富的人性,当周碧麟获得足够大的新视野时,“看透”世界后依然对世界葆有感性与激情,他传递的真实不仅离客观更近也离内心更近,因而在他的笔下,真实既是追求客观世界的真相,抵近事物本身,真实更是情感的真实,将个人意志注入到抵近本原的过程之中,从而熔铸出深沉磅礴的情感力量,获得精神世界亦即艺术世界的真实体验,这也是艺术表达走向纯熟的重要标志。这种特征,在他对亲情友爱、古俗今风以及时代之光等的抒写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从前的树》中,以树的栽种或砍伐折射时代变迁,对时光的怀想中也对生命与自然进行了感性思考。
周碧麟的散文,注重在叙事与抒情中构建出精神张力。回顾散文的嬗变,从诸子散文开始,每当新的文体形式产生,散文就从“大散文”向“纯散文”迈进一步,逐渐形成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以及形散神不散的文体特质。当代散文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在叙事和抒情这两条双曲线之间摇摆蛇行,并在叙事与抒情的融合嬗变中生长出非虚构这个接口。从根本骨架上看,周碧麟散文整体上也没有脱离“五四”建立的文学传统,尚在非虚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等更细的探索中划分出新边界或构建出新形体,但在精神气质上仍打上了不同时代的鲜明烙印。
在叙事和抒情之间,他崇尚的是质朴自然,不曾在形式上进行探索,但他在叙事与抒情的并行和对既有形式的跟进中,通过情感与文化构建精神张力,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形式意味。我常常在想,世界就在我们眼前,无论大而言之抑或小而言之,究竟该如何表达事物的意义和意思?一切事物之于人而言,倘若既无文化加持也无情感浇注,该是多么地苍白枯燥!周碧麟散文的韵味,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谙熟土家族文化,对生养他的大地饱含深情,他在自己的视界中以文化和情感加持,使叙事和抒情在相互吸引与对抗中融为一体,生成个性化的意义和意味,流露出独特的声气和腔调。这种特征,从最早出版的《推磨谣》到他的新著《高山之上》,他善于将碎片化叙事融入到情感表达,以细节凝结情感意象,在张力形成中传递出精神力。
周碧麟的散文,传达出豁达通透的人生价值观。散文不是基于公众的政治理想,它基于个体存在什么也不想干,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与文本之间的自在自为。文学是属于个体的人,它之所以被公共世界接纳,是因为它在公共世界展现出个体精神的可贵,同时也因为它在现实中还可作为某些有用工具。但文学从来就是以个体向外发散的精神之光,而公共却是以集体名义传递的规范与理念。一个创作者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其实也显得极为重要。一个作家的通透与否,很大程度在于是否明了文学与他者的关系。显然,文学是需要入世的,但同样需要是出世的,但就是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天然形成了自在表达。一切表达都是有取向的,但作家的表达很可能不是去安慰或诠释世界,甚至也不是从世界去寻找安慰或理解,它有时就只是一种内在表达。
周碧麟的表达兼而有之,当他面向纯粹自我时,他表达出一种无为的通脱透彻,而当他面向火热现实时,他传递了鲜明的个人倾向。这样的表达所呈的理念,有时是无为的,有时又是有用的,但二者并不矛盾,也许就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得以贯通。周碧麟散文呈现出的这种通透圆润,主要源自他对原生态的热爱与尊崇,他无意间已去除杂质,切净不必要关联,任由原本的我、看到的本相和情感回响流诸笔端。我想,这或许也是文学为人生的本初意义,也是周碧麟散文的又一价值所在。
周碧麟的四部散文集,《推磨谣》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一种较为传统保守的表达,《走不出你的情怀》则在题材与表达方式上尝试有所拓展,《远方何处》以宏阔视野将笔触伸展到世界的大好河山,《高山之上》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向乡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回归,它们所整体上呈现出来的,正是生命与情感在对故乡的逃逸与回归中的嬗变。这种隐秘嬗变,展现出他在艰辛探索与不停歇中所追求的个性与变化,逐步将文字之美、情感之纯、生命之真和思想之透融为一体。由于他将目光聚焦于无限丰富而复杂的生命与情感,即使在察觉真相后依然对世界保持着真诚与热情,使他的创作具备进一步走向深广与宏阔的可能,或许他也属晚熟型作家,不知道在未来的散文创作中,周碧麟还将带来哪些新质的体验,在人性与情感的无限中,呈现出何种繁复的表达式,但却值得我们再次期待。
是为序。
【本文作者简介】
凌春杰,1971年2月出生,2002年迁居深圳。1989年开始写作,先后有文艺评论、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在各类报刊发表,已出版小说、散文、评论等著作9部,曾获中国土家族文学奖、全国产业工人文学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部分文学作品被译为英、韩、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等语种,小说《跳舞的时装》被选入中蒙建交70周年纪念活动《70周年70位作家70篇小说》及《韩中作家小说精品集》在蒙韩两国出版发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本文作者凌春杰
(供图:《高山之上》作者周碧麟)